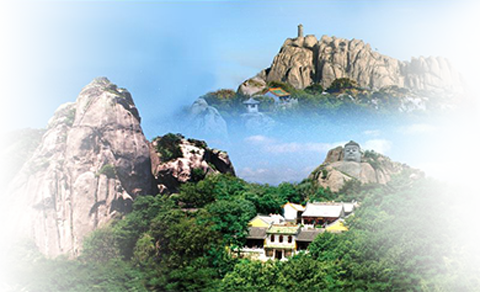让法律成为正义的堡垒
——电影《纽伦堡审判》带来的思考
中院 王学文
“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束缚。”
——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一)
由美国导演斯坦利·克雷默拍摄的电影《纽伦堡审判》,是根据纽伦堡第三轮审判(对德国在二战中为纳粹服务的法官和司法官员的审判)改编而成的,它高度还原了当时那段历史,也展现了邪不压正的真理以及人们对正义与和平永恒追求的精神。
电影是围绕同盟国如何审判在二战中为纳粹服务的法官来展开的,同盟国的检察官劳森上校指控被告席上以恩斯特·简宁为主的四名前德国法官,依照纳粹德国《种族净化法》,判决对一个智力低下者施行绝育手术,还将曾与少女产生绯闻的犹太男子费尔登斯坦判处死刑。检方指控站在被审席上的四人是纳粹迫害无辜者的帮凶,他们要对纳粹犯下的罪行负责。
面对检察官的指控,四名被告人拒不认罪,而以“恪守职责”为由,提出自己不应该为屠杀等暴行负责,尤其是前德国“司法精英”恩斯特·简宁,用沉默来表示对法庭的抗争,在天生具有“伟大法律头脑”、法学理论功底深厚的他看来,这场审判纯粹是一场闹剧,是一场战胜者对战败者秋后算账的“政治秀”。
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一系列精彩绝伦的辩论。
简宁的辩护律师劳尔夫为其所作的辩护几乎无懈可击,其慷慨激昂的辩解,几乎说服了法庭内外的人。他说简宁是被纳粹压迫,应无罪,还指出简宁利用自己法官的地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了更加恐怖情况的出现。
但是,当简宁在看完集中营大屠杀的资料片后,了解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死于集中营的真相时,终于承认在“绯闻死刑案”中,自己在审判前就已经决定判处费尔登斯坦死刑,因而在法庭上否认了能证明费尔登斯坦无罪的证据。
简宁的忏悔令人印象深刻:“我比他们更恶劣,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什么,可我还和他们同流合污。”
随着法庭各种物证的展示,揭露出了被告人的暴行以及纳粹法西斯对犹太民族等无辜者惨无人道的罪行,审判席上的大法官海伍德指出:“被告人的行为违反文明社会的共同原则。国家不是石头,而是人的延伸,正义、真理、个人的价值,是国家的基本价值。”经过审判,被告人最终被绳之以法,纽伦堡审判捍卫了正义与人性。
(二)
影片中控辩双方的辩论高潮迭起,主要涉及“二战”后对战争罪犯审判之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法理争论,但是,片中大法官与前纳粹法官之间的交流已经远远超越法庭本身,直击人性的内心,更加引人深思:
一是法律不能有悖伦理。卢梭曾经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律应当以正义为核心,应符合人类社会的伦理和道德,如果不是,那么,这个法律就是非正义的,就不应当服从,这就是所谓的“恶法非法”。
法律作为一种他律性的规范,如果有悖基本伦理,必然会缺乏民众的认同,也终究形同虚设。因此,只有以公义代替强权,以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作为基础,人们才能在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制定广为认可的规则,才能培植民众对法律的信仰。
海伍德法官对简宁等人有罪的判决,也代表着纽伦堡审判的基本立场:对法律进行判断的标准必然是伦理的、超出法律之外的,它决定着法律的核心,并永远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以人类共同的良心和自由为基础确立规则,彻底避免“恶法”的制定和执行,那么,任何违背良知的罪行就没有“避难所”。
二是法官应该恪守良知。正如检察官劳森在起诉书中指出的:“被告席上的法官丧失了法官应有的品格。”被告席上的四人中,伊米·哈恩对纳粹德国顽固效忠,即使观看了集中营杀戮的资料片,仍旧冥顽不化地辩解道:“我们不是刽子手,我们是审判员。”
弗里德里希·霍夫斯特德机械地坚持:“不应把个人的感情带到权威的法律程序中,不应怀疑法律的公平和公正性。”
沃纳·兰普缺少基本的判断力和想象力,从而为纳粹所利用,双手沾满无辜者的鲜血。
而恩斯特·简宁作为著作等身的法学教授,有着极高的法律素养,一开始也不承认判处无罪的人死刑是自己的错误……
“违反和平罪”、“危害人类罪”及“反人类罪”等罪名的确立,标志着纳粹在战争中制定的、明显有悖伦理的法规成为“恶法”,而执行这些法案的前德国法官,也毫无疑问应当以罪犯论处。
因为,如果一项法律本身已经违背了人类的基本伦理,执行者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那么这个执行者就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原则和良知。毕竟,法官是执行法律的人而不是机器,他应当具有基本的良知,有基本的判断能力,这也是法官应有的品格。
三是社会需要良法善治。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影片的最后,海伍德法官把罪恶归结于文明化程度。的确,如果法律不能对这样的大规模罪行作出正义的审判,人类也就没有资格再声称自己是文明的。社会的文明必然离不开良法善治。
纽伦堡审判也提醒我们,法治社会排斥“恶法”和“暴政”,任何国家不得制定诸如灭绝种族之类的恶法,不得实施屠杀平民等有悖伦理的暴行。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治社会之下的法律,必须是自然、公正的良法,必须尊重人类公认的文明准则,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法治社会之下的善治,必须是按照自由民主的程序,在良法的框架内,建立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
(三)
纽伦堡审判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无论是法官、检察官、陪审团,还是辩护律师,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对审判程序的认可,对辩证逻辑的坚持,对正义和真理的向往。
将侵略者当作罪犯,进行公正的审判,使罪犯和罪犯集团依法受到应有的惩罚,纽伦堡审判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中的巨大飞跃。
“国家出现危机时,它就是它代表的一切。我们要的是正义、真相以及人类的永恒价值。”海伍德法官以自己的宣判践行了自己的信念,即作为法官,即便在坚守操守成为最不可能的时候,仍然要挺身捍卫正义,只有这样,才能让法律成为正义的堡垒。而这,恰好是被告席上的前德国法官在担任纳粹法官期间所没有做到的。
良知是人类生存的底线伦理,纽伦堡审判超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其引发的是全人类对自我命运的重新审视,对道德、理性、善良和正义等基本价值观的不懈坚持。
如果没有这一次强有力的审判,那么,这样大规模的罪行就有可能被遗忘。通过审判来辨别善恶,伸张正义,儆戒未来,这或许是纽伦堡审判的最大意义。